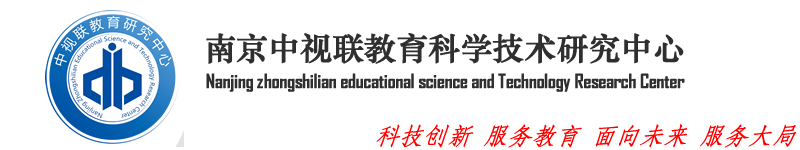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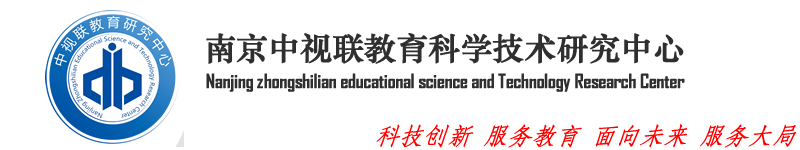

发布日期:2022-10-06 23:33 321
那么创新教育到底是不是一条离开主流教育的路线?在今天,中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创新学校,它们都在做些什么?
我们今天的对谈,就从中国创新学校的这些“基本面”谈起。
张喆:那我就从我所经历的创新教育开始谈起。我之前工作过的两所学校——一土学校和探月学校,都在北京,分别覆盖了小学、初中和高中。所以很巧,我在五年时间里,参与了整段K12学校的历程。
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。我可以地域为划分,来描述一下中国创新学校“版图”。
从北京开始,北京低龄段创新学校中比较有名的,有「一土」,包含小学和初中;然后有「日日新学堂」,也是有小学、有初中;另外还有「爱哲」(爱哲安民未来学校),也是一所创新小学。爱哲是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」的马志娟老师创办了。然后就是「探月」,探月学院是一所高中。
那么说到北京的创新学校,最出名的就是这四家。然后从北京往南走,到上海。常常会有人问上海的创新学校有哪些?但上海的创新学校其实很少,只有平和教育集团下面的「筑桥小学」,在创新教育维度里面做得比较多。
然后上海还有一个不太知名的幼儿园,其实挺创新的,叫做「绿种子童园」,在上海这是一个挺小众的幼儿园。
再往南,广州的创新学校中,有一所很特别,是一土的分校,但是开在老牌民办学校华美实验学校里面,以一种实验班的形态在发展创新教育。
同时广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教育领域,那就是职业教育。广州有一个「科蚪实务学堂」,学堂最早在北京,是给打工子弟和城市边缘人群创办的一所职业学校,后来搬去广州。
广州再往南就是福州了。据我了解,整个福建地区好像只有林老师的「福州云开学校」是一个很完整的K12全日制学校。
再看深圳,深圳有个叫做「加贝村」的学校,面向低龄段的孩子,主要办学地点在深圳和大理。
「安格学习社」也在深圳,是一个针对青少年的全日制创新项目。
离开深圳,再往南就是大理,刚才提到加贝村在大理,还有个「猫猫果儿学校」,也在大理,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,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创新学校。
大理的创新教育形态很多,还有比如像「蔬菜教育社区」这样听起来很田园的学校。大理还有很多非常小的创新教育的切入点,慢慢做成一个教育项目或学校的。
再往西南地区看,就到了成都。成都的慢生活节奏,深厚的人文底蕴,都催生出很多创新教育的实践。
比如像「先锋学校」,做创新教育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。还有「好奇学校」,很多主流媒体,比如《三联生活周刊》都讲述过他们的故事。
这样从北到南一梳理,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多创新学校都是民间力量在做创新教育,那么在创新教育这一块,公办学校有没有“下场”?其实公办学校探索创新教育的也不少。
吴慧雯:这些创新学校有什么共同特征呢?
林晓云:张喆讲得特别详细,让我的脑海中马上会有一个地图,标记从北到南的各所创新学校。
要说到这些创新学校有什么共同特征呢?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:学生少,老师多。
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?还是要从“创新学校”到底是什么讲起。
“创新”这个词本身会给人一种高冷,一种很远的感觉,大众很难通过一两句话去理解这个词。实际上这个名称可能就是创新教育一个最大的误解,我其实很希望能多做一点“去魅”的工作。
前阵子我跟公立系统的好几位老师在聊创新教育,聊得特别开心,特别有共鸣。其中有位老师讲了一句话,讲得特别好。她说:“原来我对你们充满恐惧,你们对我们也充满恐惧,但是当我们真正坐下来对话的时候,我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本质矛盾。”
如果大家了解创新教育,就会发现创新教育发起者的故事基本上差不多。要么原先是老师,然后离开体制,做创新教育;要么是和教育没什么关系的人,因为生了孩子,就想去做教育。是基本上属于后者。
我做创新教育10年了,现在回过头看,我觉得当时有两个特点:
一是人特别感性,在一种冲动之下,一种作为母亲的伟大情怀之下,就直接冲了进来。
二是无知。真的是无知,对教育非常深刻的无知。
然后10年过去了,我觉得我开始大体知道了创新教育的门在哪里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,核心原因在于,你在冲进来之前,其实是不知道——教育不是一个可以乱做的东西,你要有大量的学习和实践。
那么在大量学习的时候,你会发现,所有好的教育理念和理论,早就写在所有的教育史和教科书里了,100年前就已经写好在那里了。
创新教育的本质理论和逻辑,不是现在才写的,是100年前就有的,比如杜威的理论,比如维果茨基的理论,这些理论如何都能够落实到真实学校当中,那么这些学校就已经能够好的不得了了。
但真正的问题在于,那些好的理念、好的理论能被学校执行到什么程度。
如果理性去思考这件事,其实不是“教育”不好。“教育”很好,包括国家教育部发布的课程方式、标准、大纲,如果认真去读每一条,全部都对,全部都很好。问题就在于一所学校能够实现多少?
这种付诸实践的困难,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很深感受到。我觉得张喆应该是很有感受的。
最近我遇到好几个公立学校老师,公立学校对我们这种学校完全不了解——而我们在福州当地被称为网红学校。聊起来之后,她们就说了这样一句话,让我印象很深。她们说:
“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,你们在做的事情,就是我们想做、但还没做的。的确,从理论层面,好的教育是有共识的,很少有人会去反对这种共识,反对教育的理念,但问题就在于如何执行、如何落地。”
张喆:我特别赞同林老师所说的,我还想分享一点,其实在公立系统里面,有非常多优秀的老师。
为什么这么多好老师加在一起,却不能做到理念的落地?我自己的感受是,其实是一个组织形态或是学校系统的关系。
一所创新学校,它在落地的时候,是以一种真正的团队协作的方式落实教育理念;但传统场景中,更多依靠个人的力量去执行“教育”。
其实不同的学校,面对的外部阻力可能都是差不多的,但不同的组织方式,凝聚起来的力量就不一样。
比如我当年在一土的时候,我们在坚持做教育部规定要做的事情,与此同时,北京的大部分学校都在超前学习,带着学生往前赶。
在这种环境下,一土要坚持把教育的理念扎实落地,其实就会有“同行压力”,但团队的力量帮助一土把该做的事情不折不扣地带孩子做到位,这不是靠一个老师能做到的,不管这个老师个人能力有多强,都很难——这必须要靠一个组织,或是一个系统去把它做到位。
不久前,《光明日报》报道了深圳的「零一学院」,这是由清华大学“钱学森班”联合创办的一个开放式创新学院,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泉水担任学院院长,面向全国高一学生挑选有科学兴趣和潜能的苗子。这些孩子可能未必上清华,却可能从一个更创新的角度和环境,去进行他们的学术发展。
我的感受是,这将是教育创新发展中非常标志性的一件事。
那么还有一些公办学校做创新的例子,包括「北京十一学校」、「北大附中」等。据我了解,北京十一学校的李希贵校长将在北京办一所新的学校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被更多人关注的现状。